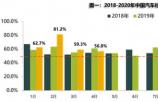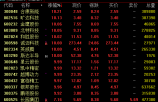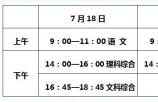如果要问对这个时代最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大趋势是什么?可能很多人都能答上来——人工智能。面对新技术挑战,首当其冲的正是对于未来人才培育的大学。
5月19日,国内率先设立人工智能本科专业高校之一的同济大学建校112周年之际,在著名人工智能专家、校长陈杰的支持下,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与设计创意学院联手举办“未来大学论坛”,提出“未来如何塑造大学?大学如何塑造未来?”的命题,邀请来自技术、传媒、教育、设计、哲学等各行业专家与大学校长、学者和学生们一起,以超前的思维和创新的视野对大学在未来的各种可能性作了一次开放性的探讨。
构建未来
模糊大学边界设计改变乡村与社区
●娄永琪(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
娄永琪教授曾是一个建筑师,2004年,当他设计的学校落成时,被评价“真美、像一个园林”,娄永琪开始反思:一个学校像园林是件好事还是坏事?于是,最近十年,用他的话说就是在“拆墙”。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娄永琪谈道:“中国大部分大学都是由围墙圈起来的,但大学和社会的界限、和城市的界限不应该这么明确。”
他理想中的大学是一个“道场”,有理想、有思想、有社群。各种各样的知识、资源、人群、事件、活动的交互关系构成大学里学生在学习,老师在教学和研究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每个人学习和成长的轨迹都可以不一样。他从“拆墙”谈到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强调学术与实践、设计与生活、创新与日常相融合的理念,向大家介绍了设计创意学院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区融入、生活方式引领到创新转化等不同领域的案例和成果,其中包括“设计丰收”和“NICE 2035”。
12年前,娄永琪教授启动了一个叫做“设计丰收”的城乡交互设计研究项目,并选择上海崇明岛仙桥村进行实践,包括改造民宿、建试验田、蔬菜大棚、体验大棚等,形成了城乡交互的典型案例。对于娄永琪教授来说,这个项目最大的意义在于,在行动中逐步明白中国未来的乡村应该是什么样的。
“未来的乡村振兴的核心,是能否创造性地破解产业难题,催生新的社群和文化,而不能仅仅想着商业和旅游。中国要走出和片面城市化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就是城乡交互。”今年,娄永琪提出了“设计丰收2.0”计划,希望通过设计思维,众筹一个以循环经济为特征的2平方公里的产村融合的复合社群。
此外,娄永琪教授还发起了“NICE 2035未来生活原型街区”,推动了大学和社区的融合互动。他们和四平街道合作,在社区众筹了一系列面向2035年的实验室。娄永琪教授表示:“大学是年轻人才和思想、研发集聚的地方,应该主动把这部分资源外溢到社区,将社区从城市创新的终端变成源头。”
娄永琪教授谈到学院陈永群老师主持的一次研究,一位居住在上海弄堂几十年的居民因为空间狭小,将刷牙的水斗装到了窗外,于是每天刷牙都是“推开窗,边刷牙,边看风景”。“这个场景非常美,这种设计是被生活倒逼出来的。社区中人们的生活智慧,是创意设计的宝贵来源。”说到城市更新,娄永琪教授补充说:“为什么很多这样的项目会死掉?因为往往只设计了物质空间,没有设计它的魂。如果你不设计业态、运营和管理,而只设计它的外观,它怎么可能活呢?”
无论是设计丰收,还是NICE 2035,娄永琪和他的团队想要做的,是为这个世界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对话未来
人文科学不能失去介入技术生活世界的能力
●孙周兴(同济大学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
新京报:你为何要发起这次“未来大学论坛”?
孙周兴:之所以要发起这个论坛,是因为技术工业加速发展,大学和社会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说实话,讨论未来是有风险的,因为未来还未来。但人本质上是可能性的动物,是向未来开放的,是在对未来的筹划中展开生活的。所以我们还必须进行这样的讨论。
新京报:随着你在演讲中提及的“人类世”的开始,技术发展愈来愈快,人类将更多地转向非标准化的、机器无法完成的工作。在你看来,是不是已经出现了技术“倒逼”大学改革的情况?
孙周兴:地质学家和哲学家把1945年标识为“人类世”(Anthropocene)的开始。所谓“人类世”意味着技术统治地位的确立,人类成为一种影响地球存在的力量。以我的理解,也意味着“自然人类文明”向“技术人类文明”的转变和过渡。大学和一般而言的教育制度是为自然人类文明而设的,对应于自然人类文明的知识形态,而未能对已经形成的技术生活世界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
大学当然也在改变自己,但也经常成为一种僵化的和保守的力量;面对现代技术的加速进程,今日大学学科建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变得不合时宜。这虽是全球普遍现象,但恐怕在我们这儿是最明显的。比如我所在的人文科学,好像永远是文史哲三门,不管世界如何变化,我们都可以躲起来缅怀过去,虚构历史上的美好时代。
人文科学如果失去了介入当今技术生活世界的能力和责任,它不被边缘化才是怪事一桩了。
现在新技术咄咄逼人,确实是形成了一种倒逼之势。我曾经说过,今天的大学可能会面临这样的窘境:一些专业的学生被招进大学里读书,四年毕业后发现这个行业已经消失了。这听起来像开玩笑,但显然不全是笑话。
新京报:你在讲座中提到,人工智能对人文科学的影响是最突出的,在未来时代里,数码知识与人文科学的关系将变得更为紧张,能具体展开说说吗?未来人文科学的教育应该是怎样的方向?
孙周兴:今天以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为标识的“数码知识”已经成为主流的知识形态,而且必将对艺术人文科学造成挤压和冲击。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原本属于人文科学的一些领域被技术化的数码知识所占领,比如学术翻译,恐怕很快会被机器翻译所取代,又比如古文献整理,将很快不再需要自然人类来做了;二是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表达方式,也将越来越技术化,近世社会科学的兴起本来就是这方面的表现;三是人文科学学术研究的制度体系越来越被技术所规整和统辖,今天全球大学和研究机构日益严密和严苛的量化管理,已经危及人文科学的生存。
至于未来人文教育的方向,我的一个猜度性的说法是,它将致力于体验-创意-游戏-共享,其基本任务是技术人类生活世界经验的重建。
新京报:你还谈到,不可数码化或难以数码化的人文科学在未来有可能发挥其别具一格的作用,哪些属于不可数码化或难以被数码化的人文科学?
孙周兴:人类的想象和创造在“普遍数理”之外,属于无法被完全形式化和数码化的艺术人文领域。这正是艺术人文科学的未来意义所在。
我不否认艺术人文科学面临的挑战,我也知道在未来的技术统治时代里,艺术人文科学是难以与现代技术相抗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言放弃,相反,为了抵抗技术风险和保卫个体自由,为了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文明状态,艺术人文科学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着力点,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何建为)

-
 杭州97家宾馆住宿降价 你想去游玩吗?杭州西湖景区风景。 江杨烨 摄3月19日,杭州市文广旅游局党组副书记阮英表示,为推动旅游市场复兴,当前杭州共有55家A级景...
杭州97家宾馆住宿降价 你想去游玩吗?杭州西湖景区风景。 江杨烨 摄3月19日,杭州市文广旅游局党组副书记阮英表示,为推动旅游市场复兴,当前杭州共有55家A级景... -
 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国景区的旅游消费便利度?游客参观武汉黄鹤楼内展出的黄鹤楼复原形制。 新华社记者 冯国栋摄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联合美团点评发布了...
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国景区的旅游消费便利度?游客参观武汉黄鹤楼内展出的黄鹤楼复原形制。 新华社记者 冯国栋摄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联合美团点评发布了... -
 2020年房地产工作怎么干?住建部:不用房产刺激经济12月23日,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住建部表示,2020年要着力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
2020年房地产工作怎么干?住建部:不用房产刺激经济12月23日,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住建部表示,2020年要着力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 -
 熊猫幼仔集体亮相 “成浪”体重已达5040克记者24日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获悉,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于今日为2019年出生的7只新生大熊猫举行集体亮相活动。在活动...
熊猫幼仔集体亮相 “成浪”体重已达5040克记者24日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获悉,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于今日为2019年出生的7只新生大熊猫举行集体亮相活动。在活动... -
 孤独年轻人撑起的“类母婴”市场你没有爱了,你需要陪伴,养条狗啊!这句马薇薇在《奇葩说》中的金句,如今真的成了很多年轻人的生活现状。宠物经济是年轻人的...
孤独年轻人撑起的“类母婴”市场你没有爱了,你需要陪伴,养条狗啊!这句马薇薇在《奇葩说》中的金句,如今真的成了很多年轻人的生活现状。宠物经济是年轻人的...
-
杭州97家宾馆住宿降价 你想去游玩吗?
2020-03-20 08:43:37
-
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国景区的旅游消费便利度?
2019-12-31 13:57:05
-
2020年房地产工作怎么干?住建部:不用房产刺激经济
2019-12-24 10:12:48
-
熊猫幼仔集体亮相 “成浪”体重已达5040克
2019-12-17 09:53:02
-
孤独年轻人撑起的“类母婴”市场
2019-12-11 08:37:40